“如果你不能引流潮流,那么你只能成為默默無聞之輩。”這是17世紀英國政治家、外交官切斯特菲爾德(Chesterfield)對人生的總結。然而,即使在今天,用這句話形容時尚業的社會吸引力仍是再恰當不過。
時尚是一門大生意。從時裝連鎖店、小型獨立的設計師機構,再到意大利、法國古色古香的建筑,市場上總有許多產品能夠切合各個財富階層、各種品位的人群。市場上一些知名的時尚品牌,譬如香奈兒(Chanel)、阿瑪尼(Armani)、范思哲(Versace)和圣羅蘭時尚品牌(Yves Saint Laurent),相對而言,這些品牌的消費人群可能只占很小一部分,但是這個富有的購買階層樂意為這些品牌支付高昂的價格。
如果將普拉達比喻為一位美女,毫無疑問她是一個掌控一切的女王。在電影《穿普拉達的女魔頭》中,梅里爾·斯特里普將這種氣質表現得淋漓盡致。影片中的時尚女魔頭,挑剔、冷傲、霸氣,事事追求完美。在時尚人士的眼中,普拉達Logo上的“MILANO”、“1913”與生俱來就有貴族血統,從一開始創辦,馬里奧·普拉達兄弟為了追求最好的品質,從全球選擇最好的原材料,將自己親手設計的皮具交給水平最高的工廠制作。由于對品質極度苛刻,普拉達皮具一上市就受到了歐洲皇室的追捧。
1978年,這個高傲的品牌陷入危機,繆西婭·普拉達接管家族事業。繆西婭·普拉達有著敏銳的設計視角,身上流淌著反潮流的血液,習慣將對立的元素整合在一起。或許,正是繆西婭·普拉達極具實驗色彩的設計創作,將普拉達從破產的邊緣拯救了回來。普拉達起死回生,繆西婭·普拉達將設計師視為企業的生命、靈魂。從1998年起,繆西婭·普拉達的丈夫、普拉達CEO貝特力發起了一系列并購,被并購的對象無一不是全球頂級設計師品牌,比如Jil Sander(吉爾·珊德)、Helmut Lang(赫爾穆特·朗)。大手筆的并購讓普拉達成為了一個能與LV、香奈兒抗衡的時尚帝國,但正是因為過于重視設計,普拉達陷入空前的危機。
普拉達為何巨虧由于長期形成的設計師文化,普拉達一直圍繞著設計師轉,這就很容易走向極端。繆西婭·普拉達曾經說過:“我喜歡與眾不同,甚至期望在設計中夾雜進政治理想,這與時尚產業天生的商業本性完全背道而馳。”這充分說明她作為普拉達設計師的商業局限性—雖然迎合了小眾的口味,卻或多或少影響了其商業格局。繆西婭·普拉達還非常偏愛以她的小名命名的品牌—MIU MIU(繆繆),這個偏年輕的二線品牌本不應該成為這個家族掌門人關注的重心,但由于家族繼承人偏愛,MIU MIU在普拉達內部被視為核心品牌。
當設計與商業沖突時,該如何選擇?普拉達近幾年來一直在做艱難的選擇題。在時尚行業,吉爾·珊德、赫爾穆特·朗是教皇級的人物,但他們和繆西婭·普拉達一樣,執著于自己的設計理想,將作品當成了一件件藝術品。但事實上,他們嘔心瀝血設計出來的藝術感十足的服飾并沒有什么銷路。2004年,Jil Sander、Helmut Lang的銷售額不過兩億多歐元,僅為普拉達集團銷售額的15%,但造成的虧損卻高達7300萬歐元。當強勢的CEO貝特力與同樣強勢的設計師產生矛盾時,就上演了設計師出走的一出好戲。并購使普拉達的規模空前大,但每年普拉達、MIU MIU兩個核心品牌的大部分銷售收入都在填補這些設計師品牌的債務黑洞,最后不得已,只能將這兩個品牌賣掉。
古琦(GUCCI)遭遇過與普拉達一樣的矛盾。它曾收購了一個設計師品牌亞歷山大·麥奎因(Alexarlder McQLJeer),雖然設計師的作品創意十足,但卻難逃虧損的厄運。設計師通常堅持用自己的方式運作品牌,不愿意根據市場變化改變自己設計產品的節奏,一旦投入到創意工作中,他們常常廢寢忘食、通宵達旦地工作。在商業人士眼中,這些天才設計師既可愛又可恨,他們無法被控制,但卻又舉足輕重。其實,一味遷就設計師顯然是不明智的,但等到矛盾爆發、設計師離家出走,后果就變得不可收拾了。
貝特力一直在尋找一個理想的品牌架構,在他的設想中,處于塔尖的核心品牌普拉達、塔中間的MIU MIU、Marc Jacobs和塔底的Jil Sander、Fendi、Helmut Lang,構建成一個固若金湯的金字塔。從陣型上看,它似乎堅不可摧,事實上卻非常脆弱。在歐萊雅的金字塔戰略中,塔底品牌是銷量最大的大眾品牌,而普拉達金字塔的塔底卻是一些沒有什么銷路的小眾品牌,它們給普拉達帶來的不是利潤,而是無窮無盡關于設計與商業的磨合與溝通。理順品牌之間的關系,可以避免直接競爭、浪費資源、損害品牌形象,并有利于形成整體優勢。當品牌之間不能形成互補、資源無法充分整合時,那么企業的多品牌戰略就是失敗的。貝特力試圖通過收購將普拉達打造成一個多品牌奢侈品帝國,可是巨大的內耗讓普拉達陷入高達人民幣62億元的財務黑洞中。為了緩解巨額債務帶來的壓力,貝特力陸續賣掉旗下的產業,專注于打造普拉達、MIU MIU品牌。
假如陸強收購普拉達我們不妨做一個意淫式的假設:假如普拉達“嫁入”中國,她的命運將會怎樣?如果對這個話題展開充分的遐想,就會發現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2008年,隨著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普拉達度過了一段非常困難的時光,盡管背負巨債,但普拉達家族一直沒有變賣股份的打算。截至今年7月,普拉達家族仍舊掌握著94.89%的股份,5.11%的股份由銀行持有。幾年來,普拉達一直在謀求上市,先后五次提出上市計劃,但最終因為市場不好而擱淺。得益于經濟衰退的減緩,今年上半年,普拉達的營業收入高達9.3億歐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9%,市場環境明顯好轉,普拉達再一次啟動上市計劃。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上海富客斯公司打算用4.5億美元收購普拉達20%的股權。然而,2009年富客斯公司的銷售額還不到人民幣40億元。由此看來,富客斯公司并購普拉達只是一廂情愿的蛇吞象鬧劇。不過,媒體說普拉達拒絕富客斯公司收購是擔心“交給中國人會把質檢、格調都變差”,這樣的理由倒有幾分可信。
在LV、香奈兒、阿瑪尼、普拉達在中國攻城略地之時,為何中國沒有一個像樣的奢侈品品牌?是因為不重視設計和品質嗎?奢侈品消費向來講究原產地,哪怕全球化的進程讓原產地漸漸淡化,但在奢侈品領域,原產地對品牌仍起著關鍵性的作用,而且它所帶來的溢價是相當驚人的。消費者能容忍普拉達換設計師,但卻非常抗拒它變成“MADE IN CHINA”。長期以來,中國產品在全球消費者的眼中是“廉價貨”的代名詞,這種固有的印象通常跟“質量差、沒有設計感”是連在一起的。所以,哪怕僅僅是產品標簽的改變,也會對奢侈品的銷售造成致命的打擊。在某種程度上,“MILANO”、“1913”是普拉達最好的品牌背書。在消費者眼中,米蘭同巴黎一樣,是全球時尚者的朝圣地,而表明品牌創立時間的數字,更能說明它數十年如一日的堅持品質。
在中國,近一半的奢侈品是用來送禮的,盡管許多消費者的消費能力尚未達到隨意購買奢侈品的程度,但由于送禮的需要,他們對奢侈品十分關注。為了彰顯身份,他們往往會為自己購買一些奢侈品配飾,這些配飾價格不高,卻能獲得身份認同。因此,在國內,奢侈品品牌的手袋通常會比服裝好賣。對一些消費能力更低的人來說,購買名牌仿冒品也有心理滿足感。正是這種復雜的消費心理,造成了假冒名牌大行其道,以至于嚴重影響了正品的品牌形象和銷路。
華倫天奴就是典型的例子,它是最早進入中國的奢侈品品牌之一,然而由于在中國多方授權,以至于品牌管理亂象叢生,再加上層出不窮的假冒品牌,致使它幾乎成為農村打工者的最愛。為了維護高端的品牌形象,華倫天奴只好黯然退出中國市場。
有鑒于此,許多奢侈品品牌僅僅將中國本土代理商視為先鋒部隊,等市場成熟后,撇開中國代理商,自己運營,例如美國手袋奢侈品品牌Coach就收回了中國零售業務。這種“卸磨殺驢”的做法是一把雙刃劍,代理商在早期推廣時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和心血,如果遭棄,必然損失慘重。為了規避這種風險,不少代理商尋求反購途徑。中國動向集團曾是KAPPA中國及澳門地區的權益持有人,但2008年4月,它收購了擁有KAPPA及PHENIX品牌的PHENIX公司;中國香港YGM貿易公司在2009年成為英國奢侈品牌雅格獅丹(Aquascutum)在亞洲的權益持有人。
從這個角度,我們似乎可以理解富客斯公司總裁陸強的心理,但仔細分析富客斯公司的業務,卻可以看出陸強并購普拉達純粹是炒作。
富客斯公司的業務模式很簡單,就是通過“直銷折扣店”售賣超低折扣奢侈品,這一模式在國外有一個特定的詞語:奧特萊斯(Outlets)。在歐美,奧特萊斯是一個相對成熟的業態,在中國卻剛剛興起。隨著中國超過美國成為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富客斯公司近幾年得以快速成長,但這不代表它能吞得下普拉達。
其實,收購普拉達對富客斯公司的業務并無多大助益,因為并購普拉達之后,必然會影響富客斯公司和普拉達競爭對手之間的合作。服裝業的每一次收購,都伴隨著設計師的流失,富客斯公司的并購也不會例外。設計師被普拉達視為靈魂,如果失去了頂級設計師的支持,富客斯公司并購的普拉達只不過是一副沒有靈魂的軀殼。更何況,普拉達是一個有著近百年歷史的家族企業,其內部關系錯綜復雜,富客斯公司接手之后必然會面臨巨大的管理挑戰。國際化并購向來是中國企業的一個雷區,TCL花了幾年時間還沒有從國際化的夢魘中逃離出來,富客斯公司如果并購背負巨債、關系復雜的普拉達,其結局絕不會比TCL好多少。
事實上,只要普拉達家族掌握了絕對的控股權,人們不會對普拉達的品質和品位有絲毫的懷疑,只要這個根基在,普拉達就會有復興的可能。但如果將控制權交給業界口碑一直不佳的中國人手中,這一根基將不復存在。在外國同行的眼中,中國人等同于剽竊創意、抄板模仿的攪局者,以至于每年在米蘭頂級服飾展上,中國人被當成不受歡迎的人而遭到國外同行的嚴防死守。在佛羅倫薩舉辦的頂級男裝展Pitti上,中國人通常會受到“特別關注”,例如拍照被沒收手機等。國外的奢侈品品牌從理念、設計、測試到上市推廣,往往需要兩年時間,而中國人習慣于通過抄襲捷徑,快速復制別人的成功。在急功近利心態的驅使下,中國企業家很少靜下心來,塑造品牌,賦予品牌文化內涵和使命感。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陸強接管普拉達后,其前途必將黯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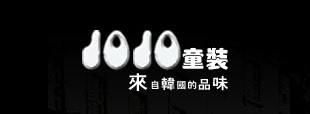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