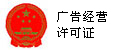時裝撰稿人Christine Tsui認為:隨著全球奢侈品及時裝業環境停滯不前,以及中國經濟放緩,中國服裝行業需要做好大規模裁員潮的準備。
中國上海——2016年第一個季度過去,并沒有為時尚業帶來新氣象,而是繼續延續了2015年的不景氣。一開年就有Hedi Slimane、Stefano Pilati等創意總監離職。而CEO們也沒有閑著,先是Chanel的Maureen Chiquet宣布離職;后有Luxottica的Khan辭職。本月,剛剛發布第一季度財報的各大奢侈品集團均形勢愁人。
《鳳凰國際》在2016年2月7日一篇標題為《美國裁員率21.8%、中國5萬億美元壞賬……22件事證明2016年也不好過》的文章指出,零售業中,隨著諸如沃爾瑪(Walmart)、K-MART、J.C. PENNY、梅西百貨(Macy’s)及Gap服飾等企業關店數量的增加,裁員規模也將逐步擴大。
而中國其實自2013年起,就時常耳聞裁員新聞。只是到目前為止,公開報道的規模性裁員事件主要發生在科技、電信及互聯網領域。而在中國的服飾行業,品牌關店消息也屢有耳聞。雖然小規模的裁員其實已經在某些局部地區展看,但是中國的服飾業是否會經歷一場大規模的裁員行動?
之所以對裁員如此關注,是因為我對裁員有切膚之痛。1998年金融危機時,我正在運動巨頭耐克(Nike Inc.)工作。一天,公司突然召開全員大會說將會裁員,但是裁員名單未定。接下來的一周,大家幾乎都是坐立不安的等待著裁員名單出爐。終于不久后的一天,一進公司,就發現電腦開不了;電話打不了了。大家都一個個被叫到老板辦公室談話。如果收到一份信,說明你被裁員了。信上說明了所有補償條件。如果沒有收到信,那么恭喜你,你對公司還有價值。裁員是立刻執行的。半天后,我周圍的桌子就空蕩蕩的了。
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資本主義的殘酷——朝夕相處的同事們突然之間走了一大半。 這次事件讓我重新審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體制的不同。至少在此次金融風暴中,沒有聽說中國的內資企業大規模裁員。一方面是中國政府做了積極的預防與管控,堅持未讓人民幣貶值;其次,從企業運作層面而言,本土企業當時正在經歷從國營向私有化經濟轉變的過程中;而私有企業則剛剛開始成長,所以那時本土企業參與全球經濟尚不算深入,也因此受到的影響并不大。不過如同耐克一樣的在中國本土市場上的一批外資企業卻經歷了一場大規模裁員。
不過,當時政府擔心大規模裁員會導致社會不穩定,以行政方式要求各業界領域的龍頭企業承諾不裁員。2008年11月22日的《東方早報》以“承諾不裁員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體現”為標題,表彰了“上海市閔行區總工…..要求區內各級工會和企業團結一致,齊心協力共渡難關,兩天內全區就有154家企業和工會響應”。也因此,當時中國本土服飾業并未出現大規模裁員潮。
只是,如今又一個十年過去了。這十年里,無論是全球市場,還是中國的服飾業,均已發生顛覆性的變革。傳統零售風光不再;互聯網已從單純的郵件通訊與銷售渠道成為一種完全的生活方式;企業中層及基層員工也從一批在家聽家長、在校聽老師、在企業聽領導的60及70后成長為更加自我的80及90后;國內的市場經濟則更加自主化及全球化。所以若再來一場經濟危機,行政干預的方法是否會持續有效?最重要的是,維護社會穩定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客觀上企業確實不具備承受能力——要知道不裁員是需要付出巨大的財務代價的:要么滅亡,要么裁員,此時企業與政府又該如何?
2016年2月2日的《中國服飾》根據國家統計局、中華商業信息中心、海關等官方數據,總結分析了2015年1月至11月服飾業的各項數據并總結出“大型零售業增長乏力”、“內銷市場動力不足”及“盈利能力下滑”的結論。從企業層面來說,到目前為止幾個領域的龍頭企業——鞋業的百麗、休閑裝的美特斯邦威及運動裝的李寧等財務報表并不容樂觀。其實,從某種角度來說,“萬眾創業”已經說明目前就業市場的困難。就業市場的困難一定程度上反應了企業至少開始在規模擴張、員工招聘上持謹慎態度。
另外,歐美公司因為長期浸泡于資本市場,及得益于發達的各類市場咨詢機構的存在,他們具備了比中國企業更強的對市場危機的預知能力。 中國企業對市場經濟規律的了解依然在摸索中,因此中國企業對市場危機的反應可能是后知后覺的。而在中國服飾業,最值得警惕的是競爭最為激烈的女裝、休閑裝及時裝鞋類。
經濟危機對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也不全然是壞事。畢竟,溫室里長大的花朵總是不如經歷過風吹雨打的草根生命力更強。 西方的企業也正是在經歷過多次市場錘煉后才成為今日的跨國巨頭。總之,時刻提放著大規模裁員的到來總是沒有錯的。